处女翻译·323《中国艺术》(120)
处女翻译·323《中国艺术》(120)
编者按:《中国艺术》(Chinese Art)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,1958年在纽约出版,上下两卷。作者William Willetts(魏礼泽)(汉学家、西方艺术史家)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,系统梳理了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、丝绸、雕塑、陶瓷、绘画、书法、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。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,“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,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”。 “让器物自己说话”,与观复博物馆“以物证史”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。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(Chinese Cultural Relics《文物》英文版)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,译者也是MLA(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)和AATA(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)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。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,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,其后附有译者注。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,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,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。 科斯岛的蚕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提到蚕的西方人。在《动物志》一书中,他提到了一种大型的蚕,“带有触角”,六月内数次变化形态。所以,“有一些女性利用这种蚕茧抽丝,然后缠线,接着利用丝线纺织布;蔻斯的一位女性名叫潘菲儿(Pamphile),她是普拉迪厄斯(Plateus)的女儿,据称是这种丝绸的首位发明者”。 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,以发现古代丝绸而著称,另有古代衣物的发现,这种衣服以薄如透明而招致恶评。这种衣物的穿着风潮从罗马帝国的低俗阶级向上层阶级扩散,导致了很多非议。瓦罗(前116-27年)提到过“玻璃外袍”,普利尼(Pliny,23-79年)也曾经谈到,潘菲儿“明显希望炮制一个让女人的衣裙薄如蝉翼,使他们看起来一丝不挂的计划”。虽然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信息非常简略,其所使用的术语意义不清楚,但可以确定的是,科恩布料所使用的肯定是蚕茧得来的丝绸。但究竟是哪种呢? 普利尼在他的《自然史》中,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话,但有些断章取义,并且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科斯岛上的蚕的相关描述,几乎无甚意义,并提到人们怎么使用飞梭来纺织这种丝线,为男人女人提供衣服。其记述中提到了四种树木,柏树、松树、白蜡树、栎树。虽然他没有明显的提出,蚕是寄生于这些树上生活,他提到这些树已经暗示了这一点。德梅森(Demaison)认为,这里的蚕属于Lasiocampa otus,一种野生蚕,其毛虫主要靠柏树、橡树和松树提供食物来源,而它们的茧也在白蜡树上有所发现。地中海的野生蚕蛾现在非常稀少。其实情况本不一定这样,亚里士多德谈论“抽丝剥茧”时,如果我们能体会其暗示含义,指的可能就是人类控制下的蚕养殖。但如果普利尼提到的“飞梭纺织”情况属实,那么实际情况应该不是家蚕养殖而是野蚕采集。因为他这里应该指的是那些已经破茧而出的蚕茧被收集起来,然后用缠绕方法抽丝。 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提到封闭养蚕,虽然普利尼曾经提到过“小飞蛾”,用茧慢慢包裹自身,然后被人为取走,放在陶罐里,加温养护,并喂给糠皮。不管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斯岛的养蚕业具体情况如何,普利尼实际上距离那时已有400年,不太可能说清楚情况,普利尼时代的丝绸业已经迅速衰落。似乎可以证实的是,普利尼对科斯岛养蚕的观察与另一处相距遥远的塞蕾斯(Seres)的养蚕业的描述不相吻合。但他知道,中国丝线纺织的布料和科斯岛的丝线纺织的丝绸质量本质一致。普利尼对潘菲儿的发现的评论应该拿来与他对中国丝的评论对照,后者让罗马的夫人们在公共场合穿着这种近乎透明的东西来炫耀,他为什么不能从这些衣料追溯其原材料呢?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,即他所说的科斯岛的丝绸生产,只要不是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话的部分,都是凭空想象。 处女翻译·322《中国艺术》(11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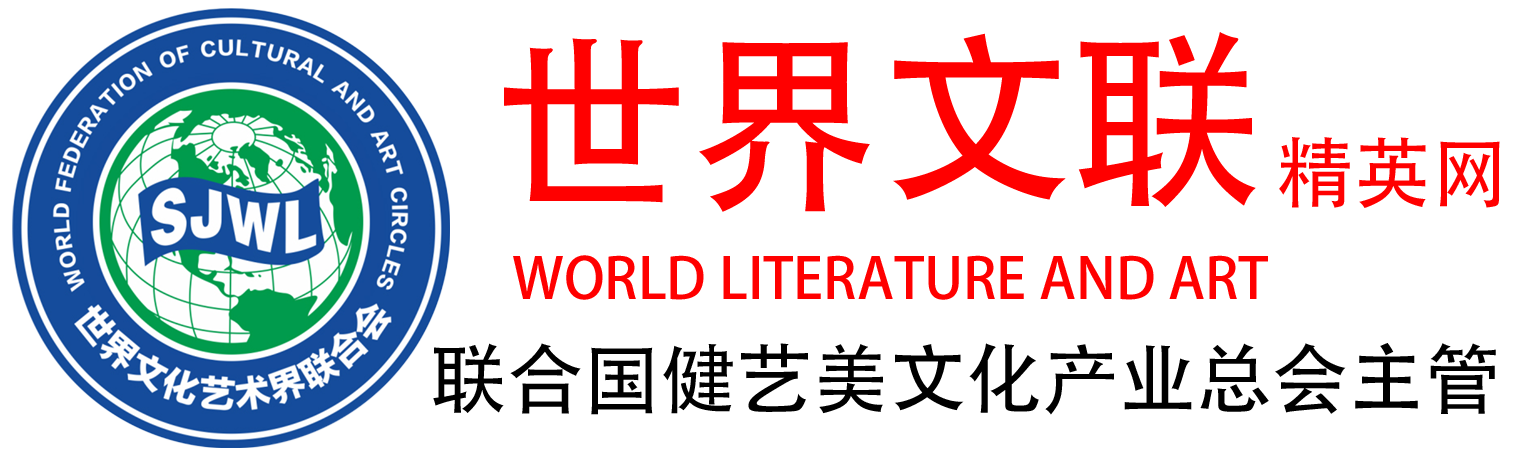
0 条 评 论 Write a Response